沈华丁琦新书《追寻》:纵有千般跌宕 人性的光辉依旧绵长
发布时间:2023-05-24 15:59:25 | 来源:中国网 | 作者:汉青 | 责任编辑:乔沐
三代著书人,夫妇皆墨客。
在文坛,传续三代的文学家族不奇,夫妇皆是作家的文学家庭也不奇,但同时满足就比较罕见了。而夫妇两人合著一本60万字的长篇小说,则未尝闻也。近日,红色革命题材小说《追寻》新书发布会在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举行。该书作者、苏州作家沈华、丁琦,就是一对文学伉俪,更神奇的是,丁琦之父丁古萍,沈华、丁琦之子沈汀,亦是名噪一时的文学人,都有诗集或散文集问世。
“追”与“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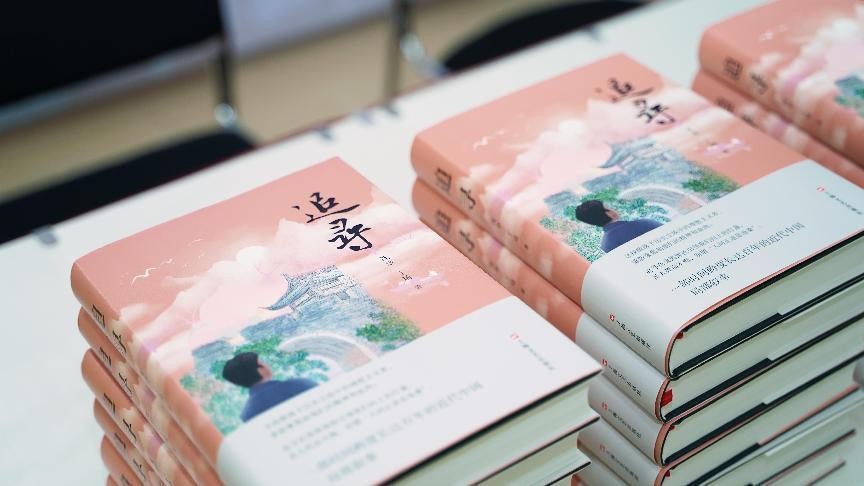
《追寻》是沈华和夫人丁琦共同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初稿长达八十多万字,讲述了从一九三七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主人公丁孜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平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阶段,虽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但始终坚守信仰,追寻梦想,初心不改的一生。
《追寻》以丁孜为着笔点,切入口甚小,但剖面甚大,地域广,跨度长,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风云变幻,创作的难度巨大。如何建构宏大的历史长卷,塑造出鲜活而带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就成了摆在作家面前待解的命题。
为了勾连起全部情节,引出人物,作者选择设置了一条隐性线索(暗线)——主人公丁孜毕生“追寻”的命运史来贯串全书。顺着伸延的线索看过去,就可以从丁孜不倦追寻的书写中,看出他怎样由青涩懵懂的少年成为须发幡然的共产主义战士;顺着伸延的线索看过去,就可以从丁孜家庭关系和社会联系构成的情境的书写中,看出其他人物的面影和身形。
丁孜的平生,大致可分为两段,“追”与“寻”。
前一段,是其寻找人生目标的阶段。丁孜起初秉承家训,东奔西颠,锐意求学,但严峻的现实教育了他,白铁匠和王汶头村民众的血,擦亮了他的眼睛;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使他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坚力量,终于在党员陈旭东的引导下,认清方向,投奔抗日民主政府。在后来的射阳县司法科工作和苏北公学学习过程中,直接接受党的教育,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树立了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前一段可以用“寻”来概括,丁孜不断探索比较,终于寻定了人生方向。
后一段,是坚守信仰、矢志追求的阶段。抗战胜利后,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他仍然坚守信念,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他总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党所交付的使命。成为伟大党组织的一员,从此成为了他的渴望。他送上第一份入党报告,但因为材料随着他逃避国民党特务追捕的转移中下落不明,入党问题被久久悬置起来了;更因为地下斗争的复杂性,青岛潜伏期间的一段,久久没有得到澄清,成为疑点,不仅影响入党,还影响到他后来的人生际遇。
解放后,随着频仍的政治运动,丁孜的社会地位一再下滑。但即使在困厄乃至陷入绝境的当口,他还是坚守信念,以共产党员标准自律。改革开放后,他恢复了干部身份,清廉自守,拒绝诱惑。离休以后,革命意志并未衰退,仍然孜孜不倦,为党工作。为了入党,他积极配合组织,弄清楚历史疑点;86岁时,又前后两次送上入党报告,直到他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忘记了许多事的时候,仍然惦记着参加党组织这件大事。
后一段可以用“追”来概括,丁孜在任何历史时期,追寻光明而宽阔的人生境界。
《追寻》通过丁孜的毕生追寻,纵向勾连,横向缀合,不露出针脚,显示出极高的文学创作水准。
艺术源于生活
《追寻》是以丁琦的父亲丁古萍为原型进行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沈华夫妇一家三代都与文学有缘,从丁琦的父亲丁古萍,到沈华和丁琦的儿子沈汀,他们都出版过诗集或散文集。三代人共筑文学梦,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家族传承和精神追求!
这部小说恰是沈华丁琦一门三代人丰富精神世界的缩影。《追寻》并未采用离奇的情节来营造夸张的艺术效果,而是写实实在在发生在平凡人身边的故事,其中的人物不少都有原型可循。作品力透纸背的感染力源于作者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信仰的忠诚。
沈华曾任苏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任职期间,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一位下岗工人曾经是江苏省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为维持生计,她经营着一个“放心100早餐”摊位,每天清晨五点半出摊,九点钟收摊,每次收摊时都会把摊位方圆100米左右的区域打扫干净。
沈华问她为什么这么做。下岗工人回答,“因为我是劳动模范。”
“劳动模范也无需把周围100米内都打扫干净。”沈华更加惊讶。
“我以前是一名纺织工人,下班前会把周围都打扫干净,才交给下一班,这是多年的工作习惯。”下岗工人回答道。
“你知不知道劳动模范有补贴的?”沈华关切地问道。
“我现在下岗了,在岗的时候有补贴,现在下岗了,就不该领了。”下岗工人回答道。
“不,劳动模范的补贴是一辈子的,国家有规定的。你是哪个街道的?回头我帮你联系。”此事过后,沈华不仅落实了这位劳动模范的补贴问题,而且每次探望贫困户时,还会自掏腰包,扶助他人。
这次经历让沈华深深地感受到工人的伟大,和劳动模范对自我极高的道德要求。这份源自生活、最真实的感动被嫁接融化到小说情节中。《追寻》后半部分写到,丁献伍等父辈们创下的阀门厂转制至他儿子手中时,一再嘱托儿子无论企业日后拥有怎样的辉煌,都要善待工人,尊重劳动。
《追寻》叙述方式质朴自然,诸多人生哲思蕴含其间。运用家庭生活细节,把人物放在具体情境文化背景中,任其在符合历史真实状态下自然而然地成长,使人物的生存环境,行为心理,有着清晰丰厚的特定历史内涵和感性形态。
在搜集素材方面,一方面由丁古萍口述回忆过往,然后沈华夫妇记录;另一方面,沈华夫妇亲自走访各地、搜集更多资料,比如前往南京采访了丁古萍的直系亲属,了解父辈的相关情况,还意外收获了一些诸如手稿的珍贵史料。第一手的素材绘就了创作过程中的饱满真实的视野。《追寻》后半部分中,丁振伍前往新疆追寻儿子的步伐,亲身感受了新疆伊犁地区变为大粮仓的这份史诗级的震撼。“我是个党员,我要以身作则,留在这里建设新疆。”小说中丁振伍儿子投身新疆建设的奉献精神是现实生活素材的艺术映射。
“在我们家族中,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遭受到不幸,而受到过家族内部不公平的待遇。在任何时候,我们彼此不离不弃。”丁琦说道,而在《追寻》中,丁琦将来自原生家庭的温暖、善良、真诚融化到小说的笔触里,最终形成了小说“行善崇德、人性不泯”的精神内核。
红色文学的全新“回归”
《追寻》是当今红色文学创作园地里绽放的一朵奇葩。它以新的姿态,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红色文学的范本。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坛,基本上是红色文学主宰。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先锋派、现代派为代表的各种文学流派陆续登上文坛,红色文学则若隐若现。直到新时代,红色文学又开始被人们重视。
但是《追寻》又不是简单的回归。小说对主人公们追寻理想的描写,呈现了红色文学新的时代特征和意义。小说秉持的多极历史唯物主义解构了昔日红色文学的二极对立思维模式,几乎是拒绝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来写它的主人公。
《追寻》的三个主人公,丁振伍、丁献伍和丁孜,只有丁孜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其他俩人都是原国民党。随着时代的发展,丁孜的两位哥哥亲历了国民党的腐败,并参与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在党的教育和丁孜精神的感召之下,发生了根本性的思想转变,深切意识到共产党的伟大,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新中国。
丁家在世纪变迁的历史洪流中,支持革命,献身革命,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中国诞生和发展的侧影。新中国的历史是由全体中国人民创造的。小说中人物所处时空、工作岗位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是爱国的,守着亲情的,从而演绎出了国家——家庭——个人的人生情怀,探求民族发展的根脉与基因,彰显了作者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
丁孜和众多人物追寻的历史,是个人史、家庭史,更是党领导下民族解放斗争壮丽史诗的一部分。《追寻》艺术再现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平等、自由奋斗的历程,立体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有血有肉人物的群体形象及跌宕起伏的命运悲欢,全方位展示了各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有助于读者对党史的理解,更加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奋斗的信念。(图文/汉青)
